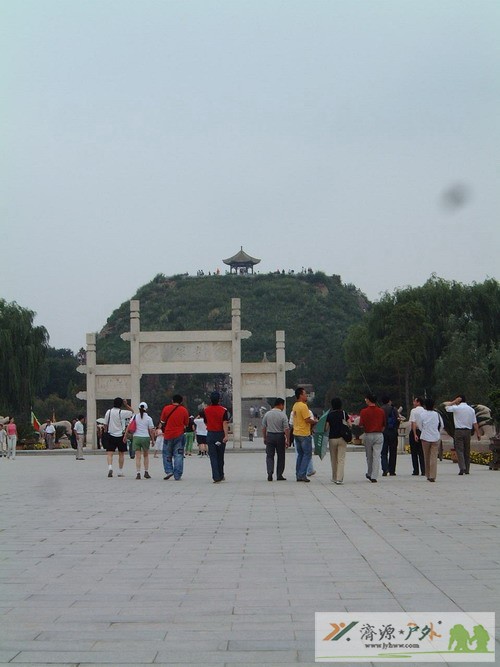走马草原(九)
我们把喝马奶酒,吃烤全羊,听蒙古歌这草原狂欢节目放在最后,作为这次草原之旅的压轴。
“有一万匹马从你的声带中跑出”,这是十几年前我听蒙古歌时迸出的一句诗,可惜上帝吝啬,只给了我一句好诗,使我不能连缀成篇,这句诗就象一个孤独的蒙古包一样,散落在我思想的草原上。几年以后,我在另一首诗中写道“野马的嘶鸣/布满褐色的鬃毛”,算是对这个孤独的蒙古包的一个聊以慰藉的呼应。
我们是通过蒙古歌认识蒙古文化的,在歌声中听到骏马充满野性的嘶鸣和马蹄敲击大地的声音,听到了草原的辽阔和天空的高远。后来看了蒙古舞蹈,发现其主要舞蹈语言皆由奔马、飞鹰、摔跤、搏击等动作中化出,英姿勃发、奔腾豪迈,益见其文化的阳刚之美。蒙古民族也许是世界上最男性化的民族,无论其歌其舞、其人其貌,举手投足、扬眉注目之间,无不充溢阳刚之气。蒙古人特有的阳刚之美在蒙古女性的表现耐人寻味,蒙古女人肥厚如大地,皮实如母兽,与弱柳扶风、体态婀娜的南方女子相对照,恍若隔世。所以当我们以南方人的眼光去扫视呼和浩特的大街时,几乎找不到一个所谓的美女。
史称“蒙藏”,蒙古与西藏之所以联称,主要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。其实蒙藏两族差别颇大,概而言之,藏人较封闭,注重精神生活,有敬畏心;蒙人很开放,喜欢物质享受,个性放纵,骑马走草原,走到那儿是那儿。藏歌高远,歌颂的是天空,有一种垂直的落差;蒙歌辽阔,赞美的是大地,是一种水平的扩展。藏歌多女性之美,卓玛姑娘长袖善舞歌遏行云;蒙歌乃纯阳之音,马头琴低吟怒吼,抒发着草原烈焰般的激情。在蒙古人看来,阳刚之美是中性的,并不一定只属于男儿,同样也应属于蒙古女性。你听过德德玛的歌吗,在我看来,德德玛的歌就是超性别的,你在听她的歌时不会在意她的性别的。
11晚8时许,我们在呼和浩特昭君大酒店临街的蒙古包中开始了这场盛宴。我踌躇良久,发现我没有能力很好地叙述一些场景之类东西,我只能勉强地表述心中所想的东西,却无法表述耳之所闻、目之所见。这是我的老毛病,我对叙述的真实性近乎苛求。我曾经说过:“我是否选择在清晰中失去真实/或者张开嘴构成O型表示深意的缄默”,表达的就是这种困惑。但现实无法回避,要把这篇文章继续下去,你必须对这个晚宴说些什么。我就这样说吧:这晚宴开始的时候已经很晚,大家都已饥肠辘辘,一闻到烤全羊的香气,禁不住口水直冒,恨不得马上撕下一大块大嚼;但是且慢,这晚宴有一套既定的程序要走,只有走完这些程序,你才能吃到羊肉。第一个程序是献哈达,在欢快的祝酒歌中姑娘给我们每人献上一条哈达。第二个程序是选王爷、王妃。我们一行十人,八位男士,两位女士。徐老板是我们中的长者,年龄最大,选他当王爷大家没什么异议。选王妃却很费周折,两位女士面子上推来让去,心里怎么想就不知道了,最后还是我拍板说:干脆你们俩全当了吧,一个大福晋,一个小福晋,今天便宜老徐得了。当了福晋以后再争风吃醋,是你们的家事了,与我们外人无关。王爷主刀开割全羊,先喂大福晋一块,再喂二福晋一块,然而才轮到我们。这顿羊肉吃得好,风卷残叶般三大盘羊肉一扫而空。有没有了?没有了?不可能吧,我们烤的是全羊,而不是兔子,有没有搞错哎?敲打了一下导游以后,又上来了三大盘。
为我们唱歌的是蒙古艺校的学生,是出来打工挣钱的,讲好二十块钱一首。三个女歌手,一个电子琴手,一个马头琴手。马头琴的音乐多来自马蹄叩击大地的节奏感、野马的长嘶声和一个人面对空旷的草原、高远的天空百无聊懒时的长吼。记得有一篇文章中说,一个人在草原上如果不吼几声,连自己都无法确定自己的存在。这话说得经典,著名的蒙古长调就是这样吼出来的。三个女歌手中有一位唱得特别好,长相也特蒙古,塌鼻梁、宽脸庞、细小的三角眼、炒米色的黄皮肤。她的嗓音很浑厚,有点象德德玛,蒙古长调唱得特别好,她也颇为得意,说这是她的专业,是跟德德玛老师学的。我们老是逮着她唱,一首蒙古长调翻唱了三回。
曲终人散,酒兴阑散时,已过午夜十一点。 |



 显身卡
显身卡